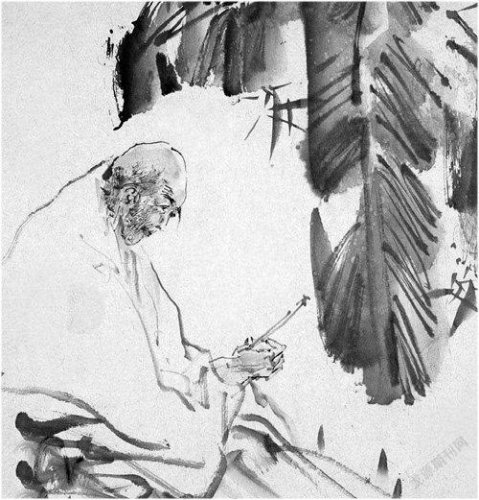精选散文:大海第一鱼(5)
大黄鱼的故事
据相关资料介绍,我国沿海地区捕捞大黄鱼的产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974 年,是我国捕捞大黄鱼最“辉煌”的一年,全国产量高达二十余万吨,仅舟山市的岱山这个小县,产量就达4 万多吨。
物盛则衰,好景不长。从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后期,反复几次的掠夺性“敲梆渔”,加上前期捕捞效益较好,沿海渔村的生产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又遇改革开放,唤起了柴油动力机帆船的不断兴起,从开始的木制机帆船,逐步向铁壳大马力机帆船发展,加上政府對渔区柴油补贴等政策的不断落实,许多机帆船都配置了卫星定位仪、应急报警、鱼群探测器等先进设施。这样,船大网大,捕捞的海域更广、捕捞的行程更远,抗风浪的能力更强。往往一网撒下,就能截获网过之处整片海域所有的鱼虾蟹类。由此,台州海域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尤其是黄鱼,产量也随之减少,价格在逐年看涨。从1983 年开始,东海大黄鱼已经难以形成鱼汛;到1984 年,全国的黄鱼产量仅只2000 多吨。直至上世纪90 年代,几乎很难见到野生大黄鱼。如果还能捕到一两条大黄鱼,那是无比幸运了。
沿海渔村都有容许孩子们上船吃鱼的习俗。当海上捕捞回来的渔船,停靠在渔西外新塘、蛎灰塘的斗门前时,村里的小男孩们,就会三五成群上船去吃鱼(渔村的风俗是女孩子或者妇女,不得踏上船甲板。认为女人身体不干净,容易玷污船身,给渔船带来晦气,这是典型的封建残余思想)。那时,沿海粮田少,多山地,人们的主要食粮是番薯和马铃薯,很少有米饭。而出海捕鱼的青壮年干的是重活,靠番薯和马铃薯这些粗粮是难以维系讨海体力活的。生产队里就把仅有的少量大米,留给他们带到海上吃。当时,米价每市斤(0.5 公斤)虽然只有1 角3 分,但远远高于黄鱼的价格。我们老家附近几个有渔船的村落,都有“鱼当饭,想饱肚还算白米饭”的说法。孩子们在家往往很少有米饭吃,到船上吃鱼,公开的理由,只是图个鱼儿刚上岸新鲜好吃的名儿,实质上是想去吃顿有米饭的大餐。
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一个周日早晨,住在隔壁的两位伙伴来跟我说,里道地的细眼同学去船上吃鱼,还吃到了大黄鱼。在那个捕捞不到大黄鱼的时代,还有大黄鱼吃,大家的心都痒痒的。说走就走,三人一起来到外新塘陡门头,找了一条停靠在那里的、还是我表哥当老大的大渔船。那条船的船头挂着一块十几米长、三十多厘米宽的旧跳板,跳板一头搁在船帮上,一头靠在岸边的泥地上。我们沿着晃晃悠悠的跳板,颤颤巍巍地爬进船里,发现已经有先到的两个小同学在那里等了。大家席地坐在船甲板上,船老大端出烧好的两大面盆海鲜,一盆是清一色的梭子蟹;一盆里面装着鲳鱼、鳓鱼等七八种鱼儿,唯独没有黄鱼。我问:“黄鱼呢?”表哥说:“哪有那么多黄鱼,出海多次就只抓到一条,早就烧给细眼他们吃了!”船上烧的梭子蟹,都在柴灶镬里蒸熟的,很鲜亮,香气扑鼻,味道还真好!但是,鱼就差极了。把那不同品种的鱼,放在镬里一锅煮,既没有用老酒、酱油,又没有姜葱蒜作料,还放了很多盐,鱼肉都被烧煳了,哪有家里烧的鱼那么鲜香和可口呢!大家的脸上无不挂着沮丧的表情。“想吃黄鱼,却连黄鱼膏都没看到。”每人吃了几只蟹,杂鱼肉大家就不想吃了。几个小朋友拿着饭碗去灶火间找米饭,没想到船老大说船上米袋早空了,米饭没得吃了,让大家多吃点鱼肉蟹肉。这时,一个大嘴巴小朋友私下里说了一句:“黄鱼不得黄鱼!这么小气,连饭也没得吃,这倒船爿!”小朋友的话音刚落,“啪”的一声,船老大就扇过去一个响亮的巴掌!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