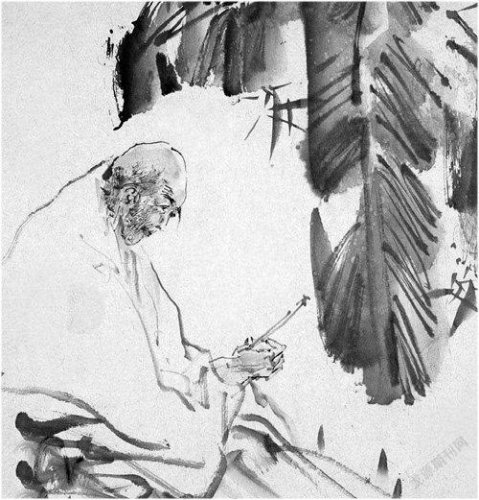精选散文:大海第一鱼(6)
大黄鱼的故事
那些年,大马力机帆船如下饺子似的入海捕捞作业,并且不断向深海、远海挺进。村里的小渔船再也没鱼可捕获了,只有停业卖船,甚至拆船卖船板。就是那次在船上没吃到大黄鱼后,延续了几十年,我一直没有看到过黄鱼。
尽管没黄鱼吃了,但外婆和妈妈熬的腌菜烧黄鱼的鲜美,始终萦绕在我的口里;再想吃一回黄鱼的欲念,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里。记得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从外地工作回来的父亲,提着一条大黄鱼到家,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要妈妈抓紧剖肚洗净先熬起来,我还主动提出去割一篮猪草作为回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满头大汗从大队桑树地里提回一大篮猪草时,家里的柴火镬已经弥漫着黄鱼肉的浓郁香味。当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揭开镬盖……没想到,这是我的一个美梦!
“黄鱼,我的腌菜烧黄鱼,你去哪里了?是谁给拿走了!”
梦中醒来,我乐极生悲,心潮汹涌激荡,如农历八月十八日的大海,难以平静,泪珠从眼眶里雨点似的落下……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调入台州市农经委工作的我,在深入乡村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现状调研时,走进了玉环芦蒲镇的几个渔业企业。在漩门湾近海养殖现场,我看到了那些浮游在海湾里,用简易木板加渔网围成的一排排“方形网箱”里的大黄鱼。逼仄的网箱里,一条条手臂大的已经发福的黄鱼,在相互挤压着、缓慢地翻动着、争先恐后地吞食着渔工从塑料勺里倒下的饵料……这就是大黄鱼的人工养殖场。后来,随着近海养殖大黄鱼技术的成功和成熟,黄鱼始终贵为稀有资源的利益驱使,在沿海浅水区或池塘中,围网养殖大黄鱼的也越来越多。但是,这样的生产环境,完全不同于深海,活动空间的有限,加上使用加工的饵料等各方面的影响,尽管黄鱼的种苗是来自大海的优质品种岱衢族,但是这些大黄鱼还是长得不再如仙子似的修长苗条,而以“臃肿肥胖”的体态出现,其肉质的鲜美度大大逊色于以往的野生大黄鱼。
在海边长大的人,普遍“嘴刁”,吃过野生的,再去吃养殖的,就会有种“食之无味,丢之可惜”的尴尬相!后来,有了大陈岛的深海网箱养殖的大黄鱼,人们都说好吃多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既然是养殖的,近海与深海还不都是在网箱里吗?难道不是一样的个头和味道吗?几次的朋友聚餐,当大黄鱼端上餐桌时,我还是不想动箸。
但是,“没黄鱼的酒席不成宴”呀。
2020 年夏季的一次朋友聚会,吃到诗友老魏带来的那两条深水网箱养殖的大黄鱼,令我彻底改变了看法。
那是两条在舟山东极岛养殖,当天用保鲜设施运到台州的鲜活黄鱼。老魏为了让大家满意和吃得开心,亲自在家操刀掌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烧好,由我开车去他家里拿到酒店的。那天晚上,当我的车子从轮渡路拐进那条拥挤的小巷,折进他住的小区,在距他住的楼宇还有四五十米路途时,一股沁人心脾的鱼香,已经萦绕在我的鼻端。真香!我不停地嗅闻着。当我提上那个脸盆大的白色砂锅回到车上,车厢里立时被一种浓郁的鲜美之气弥漫。我肚子里的馋虫已被唤醒,喉头汩汩,垂涎欲滴,此时,真想立马揭开锅盖先尝为快。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