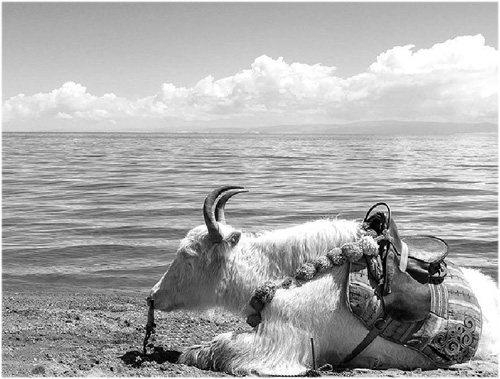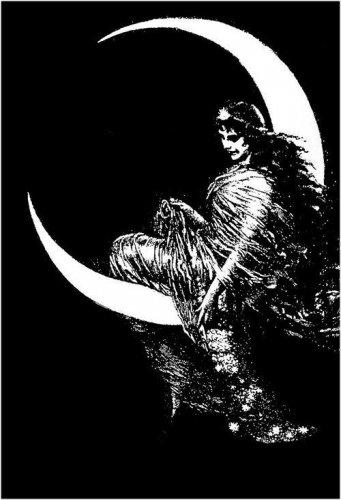生活随笔:文化老树(2)
一棵老树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 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
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我知道上了年岁的人,天再热,也不可骤冷受凉。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这也是先生挂在嘴上的荣光。先生的文字,倒未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但文化的旨趣甚至处事的态度,却颇受熏染。后来先生主持编辑了周作人的多种文集,每一种,从编辑体例、入选篇目到前言后记,都见出对周作人的独到见解。我没有附和先生的观点,便说现代散文,周氏兄弟各自开启了一个源头,且各自高耸成峰,至今无人企及。对这两座高峰,各人可有偏好,但若就文学史的意义言,拿两兄弟的文章彼此否定,则显偏狭和短见,古典散文现代化,这两条路或许永远并行不悖。先生听完,并未赞同或反驳,眼睛却为之一亮,余下的谈话,明显少了先前的生分。
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的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性。俗话说树老成精,人老成怪,先生躲藏在念楼里,似乎已将自己修成一个精怪。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
1957 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那几年,先生的确对新闻乃至政体谈了些意见。严格地说,那不是什么思考严谨的政治洞见,只是书中读到的一些常识。先生觉得当时的许多做法,违背了新闻和政治的某些常识通则,需要修改矫正。以先生当时的学识和见识,还认识不到所有常识和通则,都只就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任何旨在破坏一种旧体制和旧文化的体系性革命,所有常识通则都将被击碎。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