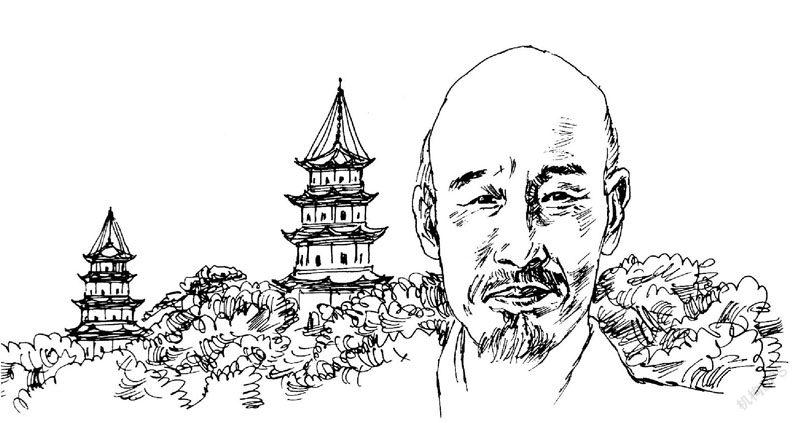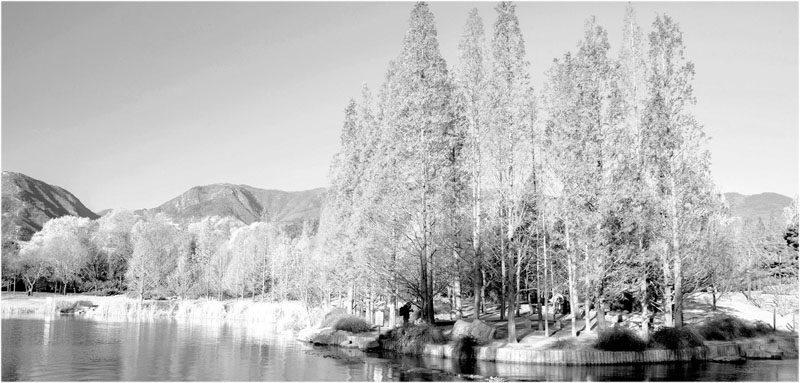生活随笔:母亲的青春年华(2)
母亲的沙家浜
也许个性强硬的母亲,至今未意识到,起初她坚决不应允的这桩婚姻最终能成,大约正是源自阿庆嫂的自信推动了年轻气盛的她。阿庆嫂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跟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凭她能从生产队一直唱到县城的本事,大抵也能把我的父亲改造成能说会道的人,能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可惜她不是阿庆嫂,父亲不是胡传魁,我老家那片地也不是沙家浜。因此,等待她的不是我父亲被改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缺少夫妻和谐互助的家,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幸福。
当她终于发现,争吵打骂即便成为家常便饭,“改造”我的父亲也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时候,她决定离开父亲。恰逢改革开放,到处是做生意的机会。那时候他们已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完成了三个孩子的生育。三个孩子成了他们旷日持久离婚战争的唯一争夺目标,双方都不愿意放弃。父亲不放弃,因为“妻离子不散”是他最后的坚守了;我母亲不放弃的原因则是,她坚决肯定地认为父亲不会供我们读书,也不会教育孩子。
那时候乡村管民政的干部也非常有意思:谁主动提出离婚,谁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好讲。外面若干赚钱的机会,帮助我母亲一年之后作出艰难的决定:离,等我挣到了钱再回来跟那个人争孩子。
放手之后,我母亲确实挣到过不少钱,但差不多每一次都因为她把自己恍惚成阿庆嫂而败走滑铁卢。起先,在外省担任一家钢丸厂的厂长,有軍队背景,生意很红火。两年后,带着挣下的家业,转回老家县城开饭店,租房、装修、请大厨和服务员,有模有样。孰知饭店这行从买菜就得精打细算,更不能图豪气不计成本大盘子大碗,每天还有那么多损耗。像她这么爽快的人,能坚持到一年半之后才关张,真真算得上奇迹。
经营不好饭店,感觉自己的强项还是去外地承包钢丸厂,于是她又带上些亲戚朋友乡亲,一起出去发财。这回她发财的根据地离我们更远,离国境线只一两百公里。钢丸厂依旧是赚钱的,她依旧自任厂长,大小事务她说了算。
有一天,被她委以重任的亲戚,因工作跟她起矛盾,心生怨气,私自卖出工厂产品,给她知道了,顿感规矩不严难成方圆,自家亲戚都管不了,还怎么管理其他工人,面子也无处搁放,一怒之下她没有把亲戚喊到屋子里轻言细语好好沟通,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甩了人家一个响亮的耳光,还不解气,把阿庆嫂想骂而没有骂出口的话,都骂了。第二天,亲戚走了,同时打包带走了其他工人,去了附近另一家钢丸厂。
工厂办不成,她打算卖饲料。别人卖多少,进多少货。她呢,感觉人家像她一样,特别讲义气,就一次性进了一车皮,五六十吨。积压资金不说,后来还发现质量问题,在库房里放了十多天就开始发霉。她去跟生产企业交涉,发现那个乡镇企业已经垮了。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