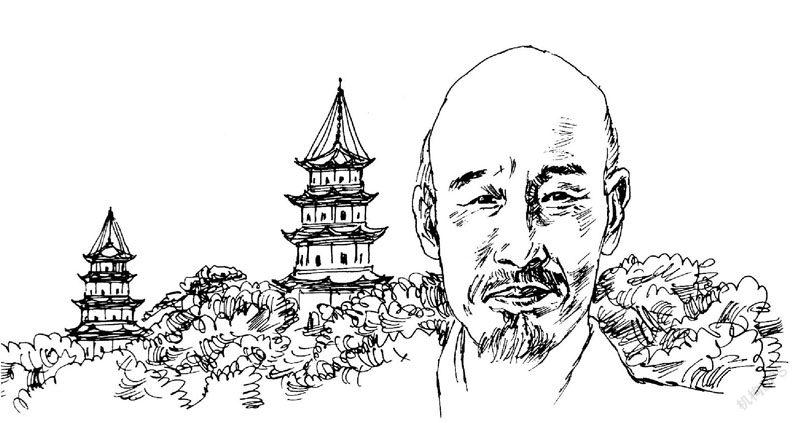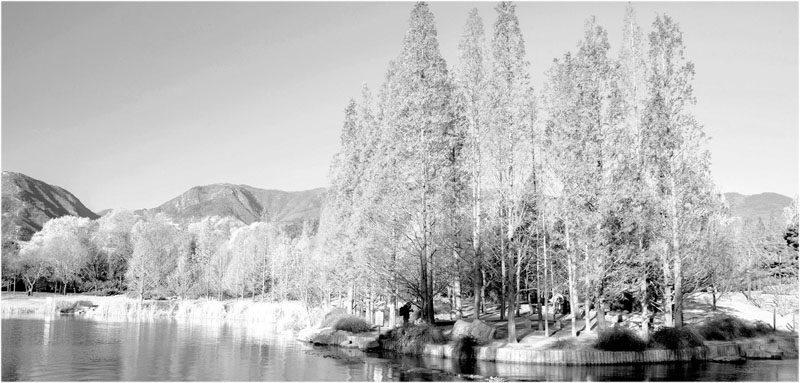生活随笔:母亲的青春年华(5)
母亲的沙家浜
石坚易碎,刀硬易折。这道理她也许至今没有悟出,也许悟出了,只是赶不上她大喊一声“刁德一,贼流氓,毒如蛇蝎狠如狼”来得干脆直接,响亮痛快。于是无论是亲戚朋友邻居,还是长途车上素昧平生的陌路人,只要有不平之事,她笃定能够凭一腔热情,仗义执言。那情形下的母亲,豪气干云,我总感觉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而已,但是鲜明地写在她脸上:“这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往往受伤的是她自己。如果一群人都受伤,最受伤的,还是她自己。
至于对孩子的养育,我用我的亲历作证,她愿意倾尽所有。假如她有足够的钱财,把亲戚朋友邻居中贫寒人家的孩子,以及街头巷尾那些没家可归的孩子,全都养起来,那是她非常向往,很乐于去做的事情。
在她生意顺畅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她都带许多东西和钱,来看我们姊妹仨和我的奶奶。她说她跟我父亲没有关系了,但我奶奶依然是她的亲人,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次她来看我们,父亲总说:“你们的妈又来收买你们了!”“收买”这词,对买方和卖方,都不是好词,也就是只用在坏人身上。可是,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她来收买我们。她给我们带来书包文具和零花钱,带来体面的衣服和短暂的我们都不敢直视的母爱。
在父亲的屋檐下苦熬的日子,跟好多农家女孩一样,好好念书,初中毕业考取卫校或者中师,端到公家饭碗,解决温饱,就是我明确而又近切的目标。
然而,母亲不同于乡村屋檐下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农家女,她终身抱憾于她的母亲,用一根吆喝牛的细竹棍,将她从教室打回家里。她了解到自己女儿成绩还行,便掷地有声把“高考”这个词带进了女儿的生命中。由此,她也为自己又走上一长段毛刺和荆棘丛生的逼仄小道埋下伏笔。实在无法维系我的生活费时,她做了她极不情愿做的事——回过头写信求我父亲,拿出点钱来支持一下我的学业,这钱算是她借的,等她手头宽裕了就还。偏偏高中学习并不那么争气的我,被那些门门优秀的种子选手甩出几条大街。我那沉默寡言又固执己见的父亲,他的眼睛怎么可能从自己沉默寡言的女儿身上看到一丝投资能收效的希望呢?农家地里的物品,能换回来的几个钱儿,本就十分稀少,珍贵,一旦存进折子里,他便断无再把它取出来花掉的念头。
我的父亲硬着心肠不愿资助我读高中参加高考,几位乡邻的话,不无推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在上街赶集或下集的路上,遇到我父亲同行,各自都喜欢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父亲说:“老表,我看,你辛辛苦苦养这些娃儿,不划算哦。过年过节,只要娃儿***一回来,三个娃儿齐整整的,麻雀一样都飞到她那里去了……”然后毫无内容地尬笑几声。我们的父亲脸僵僵地说一句:“腿长在各人身上。”说完这几个字,便木在那里,不再吱声。其他人一时也不说话了,只有他们赶路的脚底板发出不停歇的踩踏声,在乡间小路上回响,直到某个健谈的乡人嗓门里蹦出另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浓重的沉默才打破。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