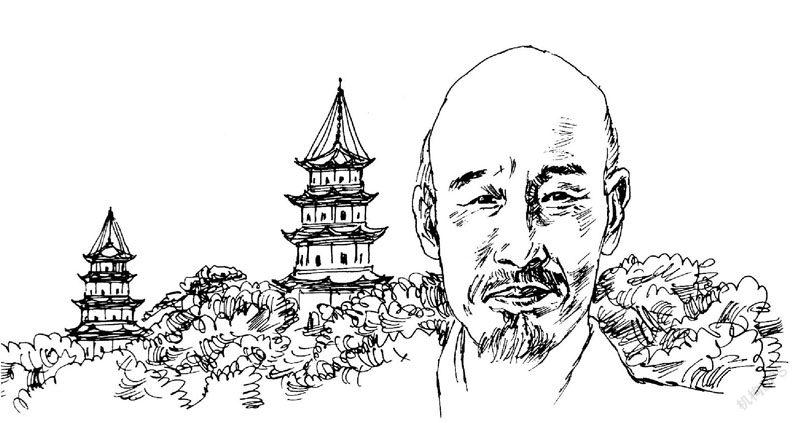生活随笔:母亲的青春年华(6)
母亲的沙家浜
母亲的生意陷入困顿蹇劣,我的高中才上到一半。有一天她独自回故乡,跟我们姐弟在县城短暂相聚。夏日午饭时分,她在餐店给我们点了稀饭下肉包,她自己却只吃稀饭下一小碟泡菜。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和吃不来肉包”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前也没听说过。
一次分别,往返于城乡的班车上,坐着和挨挨挤挤站着满满一车乘客。想着就要出远门的她情形的不好,即将回乡下父亲家过暑假的我,低垂着头站在车门边,一言不发,担忧和焦虑毫无保留全写在脸上。其实内心也生着她的气,积压着对她的抱怨,抱怨她自由选择的第二次婚姻,为什么还是没能让生存养家的路走得稍微顺畅些。我不想,也没有勇气正脸看她。她却抓紧时机叮嘱我,她的事,我不需要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少去田里干农活,多花点时间读书就成。说着话把五元钱递到我手边。知道她当时全部的家当也没几个五元钱,我挪开手,不接。她把折叠的纸币塞到我手心,我还回她手心里去。紧挨我站在车门边的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不喊驾驶员关车门。还有多少人有幸观瞻了一对母女,将一张五元纸币塞过来又还回去,塞过来又还回去,我是没勇气哪怕瞥一下眼角,去做一秒钟的关注。那情形多持续一秒,心脏就多受一秒压迫。终于我不近人情地朝她低吼:“不要再递啦,我不要——!”气吼吼地一甩手臂,差不多用尽了全身力气,决绝地把纸币扔向母亲脚边的地上,然后没好气地赏了售票员一句:“你让师傅关门啊,该走啦!”
车门一闭,车子轰隆,一气冲出车站,母亲呆愣的样子很快在车窗外消失。
我不清楚,那时刻,她是否跟我一样,眼中涌起酸楚的泪,却忍了又忍,硬是没有给它们流成河的机会。
最窘迫的形势,出现在高考临近的一个月。从父亲身边要不到最后阶段生活费的我,因为高考的紧张压力,没管住自己的情绪及时收住笔,在给母亲寄去的快件信上,很直白地写了几句悲观丧气的话语。一张六十五元钱的汇款单很快寄到。交掉报名费后,余钱足够我那段日子,每到饭点,都能手中捏着足量的饭票和足价的菜票,坦然自信地往饭堂走。然而,从考完试后收到的第一封信里,我得知,我的母亲情急之下去了医院,她卖了自己的血,然后把钱寄给我。
信很短,三四行文字,是她的亲笔书写。看完一遍,我就闭上了眼睛,不想再睁开。但是我的大脑还在清晰地逐行展读那封信,一遍,又一遍。信上的每句话,我母亲书写的稚拙的每一笔画,都化成医生手上沾着血珠的针头,狂飞乱舞,扎得我五脏剧疼。我的母亲,这个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得果敢决绝又悲壮的半个“阿庆嫂”,她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可是她有没有想过:若不是她由着我死爱面子虚荣,我怎么就不能逼自己向我的老师们开口,寻求一次帮助呢?即便是實在无法可想了,也可以先退一步再作打算的;纵使执意向前,她的女儿,宁可选择其他千百种让自己忍受委屈甚至屈辱的方式,也是不愿接受她这种付出的。一副罪孽的十字架,我的亲爹亲娘,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商量,却合伙让我背上了它……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