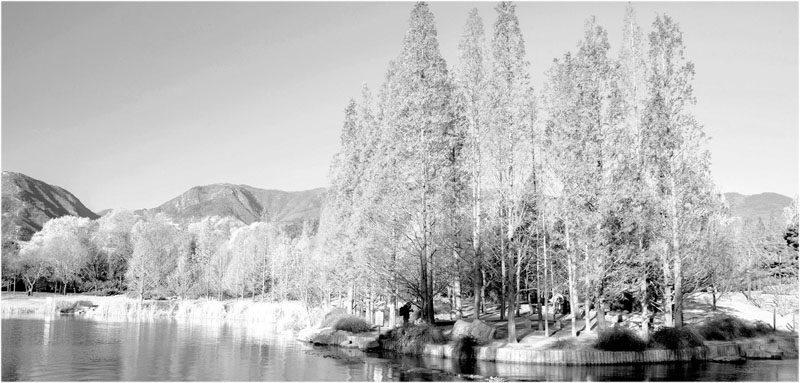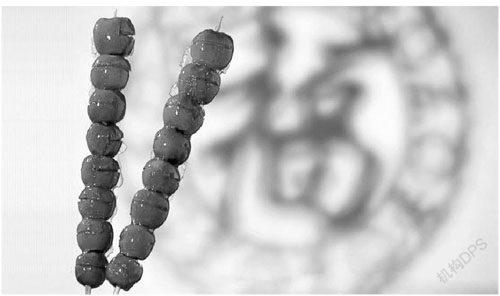生活随笔:家的故事(3)
弯弯的目光
那时交通不便,从阜宁到徐州要四个小时。母亲和卫红下地干活了,边干活边估摸我到了哪儿。看太阳西斜,母亲又说,你三哥快到徐州了。母亲没去过徐州,只是之前听我说过我大致的旅程,她记住了徐州。晚上收工回家,做了晚饭,却一口没吃,坐在灯下,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思绪飘出了老屋。夜色坚硬,把村庄封得水泄不通,唯独封不住母亲的思绪。母亲的目光轻易地穿过黑夜,穿越时空,一直追随着我。我已上了火车,没有座位,蹲在车厢连接处,低着头打盹。这些情景,母亲估摸到了。
约莫九点来钟,母亲上了床。卫红在那头睡着了。卫红尚小,倒头就入梦。母亲没睡,她坐在床头,睁着眼,看着黑黢黢的夜。夜太深,窗里窗外是凝固了的黑。母亲没有睡意,一直坐在床头,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这雨下得没日没夜了。母亲自言自语,叹了口气。想到我湿漉漉的旅程,母亲的心纠在了一起。
许是坐累了,她躺了下来。躺下来,并未睡着。她喊了声卫红,卫红睡得正香。叫了三四声,才把卫红叫醒。问几点了,卫红摸出表,说十一点了。母亲叹了口气,说离天亮还早呢。天亮了,你三哥就到北京了。卫红说,姆妈,睡吧。
母亲没睡,睁着眼,望着房顶。这房子是1972 年砌的,砖墙草盖,当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多少人羡慕啊。那时都还住着草房,农村人靠种地哪能买得起砖?父亲是公社干部,每月能拿上工资。工资不多,二三十块钱。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母亲在家养鸡养猪,种粮种棉,收成下来了就去赶集,卖鸡卖粮,攒下钱来盖房子。那时的日子苦啊,父亲在镇上上班,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家里家外,耕地收粮,推挑提扛,母亲拼了命地苦,生怕落后了别人,让村人耻笑,让父亲在外面失了颜面。终于,盖起了全村第一幢砖墙房,母亲和父亲的那份喜悦,溢于言表。后来,进入80 年代后期,农村生活好了,不少人家都盖了新房,砖墙瓦盖,还有盖楼的,比我们家强了。听母亲说,父亲去世不久,公社书记顺道来探望,看到我们家砖墙草盖的房子,感慨地说,没想到啊,何荣中是社委干部,却住得如此寒酸。
夜沉沉,雨不知啥时停了。母亲望着窗外,黑暗重重。她又叫了几声卫红,卫红没醒。用脚轻轻蹬了几下,卫红醒了,说夜里一点了。卫红说,姆妈睡吧,一觉醒来三哥就到北京了。卫红说完,又呼呼睡了。
一觉醒来就到北京了,说得多轻巧。母亲想,儿子坐地上睡觉,多遭罪啊。母亲很不安,又爬坐起来,她怕自己躺着,一不小心睡着了。儿子坐在车厢的地上打盹,她怎能安卧床上呢?仿佛她舒服地躺睡在床上,就是对不住我了。又仿佛她陪着我熬夜,就能减轻我的旅途劳顿。仿佛她睁着眼,就能照顾到千里之外的我了。而此时我坐在地上,迷迷盹盹,何曾想到,千里之外的母亲,正陪着我,遥念着我。我有时眯眼,有时被人叫醒。半梦半醒间,想的是学校的事,书本上的事。至于母亲在干什么,我没去想。何况这个时分,谁都进入梦乡了。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