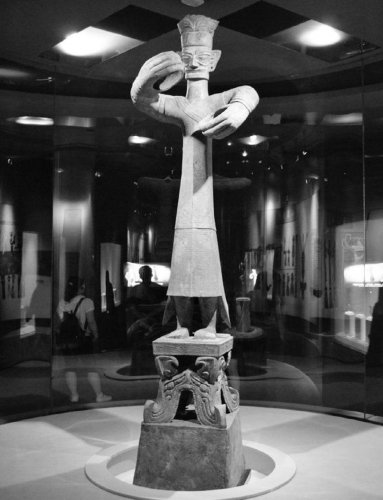散文作品:对史铁生的追思(2)
作家中的思想家
我妻子在一天上午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就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我家住的静安里,到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给史铁生送毛衣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风刮得很大,满城似乎都在扬沙。我们得顶着寒风,眯着眼睛,才能往前骑。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安忆为史铁生织的毛衣是墨绿色,纯羊毛线的质地,织毛衣的针型不是“平针”,是“元宝针”,看去有些厚重,仅用手一抚,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收到毛衣的史铁生显得有些激动,他激动的表现是举重若轻,以说笑话的口气,在幽默中流露出真诚感激的心意。他说,王安忆那么大的作家,她给我织毛衣,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当得起!我看这毛衣我不能穿,应该在毛衣上再绣上“王安忆织”几个字,然后送到博物馆里去。
我注意看了一下,史铁生身上所穿的一件驼色平针毛衣已经很旧,显得又小又薄又瘦,紧紧箍在他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稍一弯腰,后背就露了出来。王安忆此时为史铁生织了一件新的毛衣,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跟雪中送炭差不多吧。
通过交谈得知,史铁生生于1951年的年头,我和妻子生于1951年的年尾,我们虽然同岁,从生月上算,他比我们大了11个多月。从那以后,我们就叫他铁生兄。
二、听王安忆与史铁生“抬杠”
我和铁生兄交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间。那段时间,王安忆让我帮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一个人在单元房里写东西。在开始阶段,王安忆的写作几乎是封闭性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写作,也不和别的文友联系。她主动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雍和宫那里搬到了城东的水碓子。王安忆写作的地方离史铁生的家比较远,王安忆对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她每次去史铁生家,都是让我陪她一块儿去。每次见到史铁生,王安忆都是求知欲很强的样子,都是“终于又见到了铁生”的样子,总是有许多问题要向史铁生发问,总是有许多话要与史铁生交谈。常常是,我们进屋后还未及寒暄,他们之间的交谈就进入了正题。在我的印象里,王安忆在别人面前话是很少的,有那么一点儿冷,还有那么一点儿傲。只有在史铁生面前,她才显得那么谦虚、热情、话多,简直就是拜贤若渴。他们的交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艺术的;抽象的,具体的等等,可谓思绪飞扬,海阔天空。比如王安忆刚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看过了,她要听听史铁生的批评意见。比如他们谈到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同性恋者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再比如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是贵族创造了艺术,还是民间创造了艺术?富人和穷人谁更需要欣赏艺术?由于王安忆的问题太多,有时会把史铁生问得卡了壳。史铁生以手扶额,说这个这个,您让我想想。仍想不起该怎么回答,他会点一颗烟,借助煙的刺激性力量调动他的思维。由于身体的限制,史铁生不能把一颗烟抽完,只能把一颗烟抽到三分之一,或顶多抽到一半,就把烟掐灭了。抽了几口烟之后他才说:我想起来了,应该这么说。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