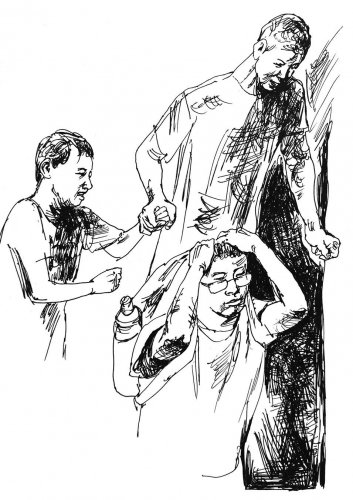生活随笔:比人类还古老的黑(2)
我所理解的黑
白驹过隙,一晃人到中年,黑已经浸润骨髓,情感杂混。好多个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直挺在床上。黑从窗外涌了进来,漫无边际。楼下的皮鞋声清脆、响亮。青春的容颜,柔软的腰身,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飞驰。那些为米粒而奔波的蝼蚁呀!两只鞋,鞋的印迹,像段铁轨,橐橐地把她载向无法预知的未来。曾经年少轻狂,深夜,不经意间,爱在楼下弄些声响,外出,抑或酒醉,趁着黑的黏稠,让青春肆意挥洒。如今,吃过晚饭,我也会出去走走。灯火璀璨的街道,流光溢彩,汽车像甲虫一样缓慢地爬行。走在街面,小心翼翼,穿过一个个红绿灯的岔道口,向东向西。不管夜色多么暧昧,走多远,我都会停下脚步,折过身,沿着原路返回。好几篇文章里,我都描述过这个情景,它镌刻于我的记忆,缱绻,挥之不去。这是我伤悲过的一切,也曾是我热爱过的一切。
是日,女儿告诉我,她们班的四个同学,下学期要分流到新建的小学。她停了停,接着说,她给同学送礼物了。我问,为什么要送呢?她说,从一年级一起念了三年,有的从幼儿园就相识,很不舍。我问,送纪念册了?她说,送了她最喜爱的芭比娃娃。女儿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表情是看不见的,但我能体悟到孩子滚烫的心,第一次经历离别的情感。我用力地蹬着车子,沉默好一会儿。她又说,同学们为什么要分开呢?我问,你们没留通信方式?她说,留了,要联系的。女儿没有兄弟姐妹,孤孤单单,常常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玩。我觉得女儿孤单,就带她到城南的市场买了两条金鱼。没过多久,一条鱼儿死了。女儿趴在鱼缸前,看着另一条鱼儿,目光怔怔,喃喃自语,说,小鱼多孤单啊!现在,女儿长大了,不再说那些痴话,可她依旧一个人,形影相吊。时光会慢慢变老,我们的青丝会变成白发,终将烟消云散,不可逆转。女儿要面对这一切,一个人,她的孤独如黑。
父亲母亲住在乡下老家,不愿随我到城市一起生活。他们说,楼房是整齐划一的格格笼子,人们成了圈在里面的鸟雀,无法动弹。我在小城工作、生活,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似乎村庄与我是件遥远的事。我是一个流浪的孩子,如飘蓬,再也回不到村庄。母亲会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的生活起居和女儿的学习,还给我们捎带蒸馍和菜蔬,叮咛一定要准时去车站拿取。母亲年纪大了,父亲的年纪也大了,家里还有我的奶奶,八十多岁,需要他们赡养。电话里,他们从来报喜不报忧,好像这个世间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事。父亲进过几次医院,动了手术,现在需要药物去修补千疮百孔的身体。有次,家里的自来水断了,父亲去村头古井担水,一次路途,需放下扁担歇缓三回。父亲的气力少了,就像小时候,我不小心,扔在草丛边的糖果,无论怎么努力,却也找寻不来。父亲母亲的电话是老年机,无法视频。每次电话,都是母亲一个人在说,但我知道,父亲在听,奶奶也在听。他们侧耳倾听,永远是人间最忠实的观众。电话那端,我听见故乡土地的胎音,每一棵草,每一株树,每一朵花,每一条虫,这些游走在土地上的至亲至爱的圣婴。可我依旧无法探知,他们的表情和日益徒添的沧桑。有时我想,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有一天,会不会突然撒手而去?我不知道,电话那端隐藏的秘密,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无法预测,永远。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