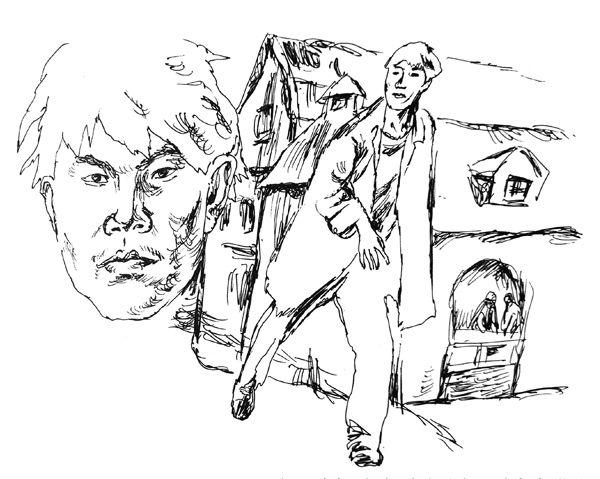文化散文:婆婆身上那种独特的气息(5)
婆婆的目光
来回看了几遍,我也没看出需要修改的问题究竟在哪儿。拿去问丈夫,丈夫一看就笑了。丈夫说,她是怕别人误解不让我参军这件事,怕人家说她觉悟低。一听到“觉悟”这两个字,我立刻茅塞顿开。婆婆对觉悟历来是十分看重的。见到有人占小便宜、不排队等这样的小事,婆婆都会鄙夷地说,这些人真没觉悟!何况是送子参军这么大的事。到底是知母莫若子,小東毕竟还是比我更了解他的母亲。
我一下子就理解婆婆这些天来的焦虑了。许多个人的心理感受,他人是永远无法切身体会的。你的伤口中流出来的血只能带着你自己的体温,即便这些血立刻就溅到别人身上,也会马上就失去原有的温度。我明白了,婆婆不厌其烦地追究那些并不重要的细节,只因为她心中不快。婆婆是认为我把她的觉悟写低了,没能把她写得更好、更符合她对自己的认定。
婆婆是极自尊的一个人。对婆婆的自尊,我素有领教。
丈夫的继父、丈夫、我,我们三个现役军人在一起谈论部队的事情,半天插不上话的婆婆会突然找个话茬儿讲起她当年在部队的往事。也是老军人的继父刚想插嘴,婆婆就抢白道,你是在地方部队,你们是稀拉兵。我是在野战军,我们可是正规部队!
婆婆再嫁后,立即去了偏远的北边,从她原来生活在沈阳的那个圈子中,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再回沈阳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婆婆和当了兵的儿子一起去八一剧场看电影。灯灭之后,婆婆才悄悄告诉儿子,后面坐着的那些军区首长和他们的夫人许多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熟人。不明就里的儿子想回头看看,硬是被婆婆拦住了。更令儿子不解的是,电影还没等演完,婆婆就把儿子从剧场里拉了出来。婆婆是不想等到灯亮后让那些老战友们看见自己,她不想见任何熟人。
我是在长了几岁,又为人母了之后,才逐渐理解婆婆的。我常想,再嫁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婆婆的内心,使她的性格在极度自尊和极度自卑的纬度上发生扭曲,使她在多年后仍无法正视、无法面对当年的熟人?我猜想,这里有着太多的因素:有婆婆头脑中残留的封建意识造成的自身局限;有从高处突然降到低处的生存窘境给婆婆带来的心理落差;有世俗的挤压和冷落;还有婆婆那破碎了的虚荣、自尊和委屈。我想,婆婆无论怎样做都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婆婆的所有行为,都只是一个正常人的人性的自然反应。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可逾越的局限,更何况婆婆多年来以其单薄之力承受了太多的磨难。
婆婆的自尊常常超过自身的需求。90年代之后,台湾的舅舅提出要来大陆探亲。舅舅在写给自己姐姐的信中说:“我准备从老家去您那里住几日。我知道大陆对老干部照顾得很好,每家都有一栋小楼、一部电话、一辆小车……”这封信给婆婆和继任公公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几天后,这两个三八年的老八路共同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赶在舅舅来之前装修房子。素来节省的婆婆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搞装修,花得我直眼晕。看到婆婆花钱的样子,想到婆婆忍着腿疼跑远路买菜和整日吃萝卜白菜的情形,我的心里隐隐作痛,但婆婆此刻却丝毫不感觉心疼。婆婆说,咱们虽然没有小楼、小车,也不能让国民党小看了我们!因为知道舅舅家里养着好几辆车,继任公公就去找干休所商量,把所里的一辆小面包車包了下来。他们当然不能让舅舅看我们的笑话。舅舅住在家里的那几天,为了保证车随叫随到撑足脸面,继任公公把舅舅送给他的烟一股脑儿都撒了出去,自己一根也没抽。我心疼他们,也理解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这样竭尽全力地做,并不只是为了给自己挣脸面。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