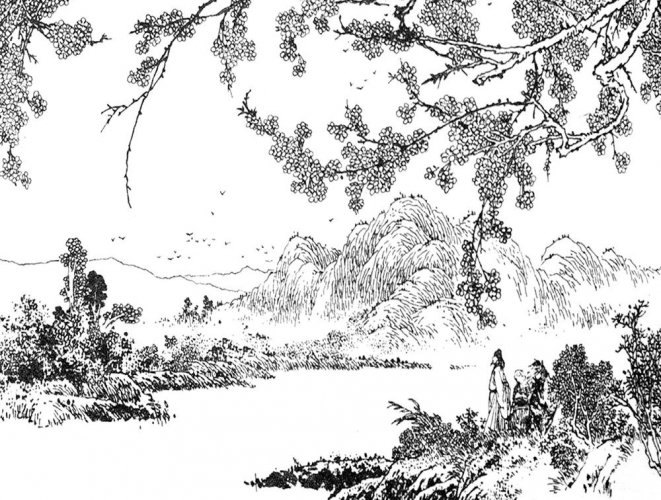生活记忆:妈妈的手擀面(3)
面条
其实,面条不拒任何蔬菜,与任何蔬菜都没有不搭,更不存在相冲相克。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条就是如此。也就是源于这种“百搭”的性格,面条才得以流传甚广,才能深入人心,为世人所好。
四
古人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面条与大蒜也是如此。吃面时怎么可以不就大蒜?都说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若是吃面不吃蒜,不仅仅是营养减半,食欲都会减半。
还记得在老家吃面时,在端碗出来之前,务必先剥上两瓣大蒜,扔到碗里。若是面中菜少,一碗面条,两瓣大蒜怕是不够,还得在手心里再攥一瓣预备着。开吃时,呼噜一口面条,先不要嚼,待咬上一小口蒜然后再嚼。蒜特有的辛辣,尤其是老蒜更辣心,会让人忍不住连忙多呼噜几口,抵消辛辣之际也能多吃几口面。此刻面条是否好吃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有大蒜撑着,怎么也得呼噜个一两碗。若是吃焖面,离开大蒜更是玩不转了。焖面比较干,吞咽之时会显得稍微费劲儿。但大蒜恰如润滑剂,先把大蒜嚼在口中,待大蒜辛辣之味散发时来一口焖面,不用细嚼就能顺溜下肚。此中道理颇有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之妙。
来到北京之后,汤面吃的就比较少了。食堂倒是经常有兰州拉面或安徽板面,而且还配糖蒜。我常常觉得可惜,那可是糖蒜啊。童年时家贫,如果赶上地里的豆角、黄瓜不争气,往往就无菜可吃。野菜什么的,早就被掐干净了。那怎么办?就得靠糖蒜了!准确地说是腌的咸蒜。糖多贵啊,谁家舍得放?一头咸蒜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菜”。最多再弄些自家晒的“酱豆子”,凑合凑合也就过来了。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就只能馒头蘸盐水了,总算有个咸味儿。我还记得父亲用热馒头蘸凉盐水吃的情形,见他大口大口吃得那么高兴,我都以为那盐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现在拉面或板面中都有青菜和牛肉,再搭上糖蒜,太奢侈了,有瓣大蒜就中了。
工作后无论是糖蒜还是大蒜都很少吃了。赶上面条,若实在克制不住就吃一小瓣,算解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因为蒜的气味实在是“难闻”。开会、汇报工作或与人交谈,要是嘴里冒出这般奇异的味道,势必招来奇异的目光。村里自然没有这样的讲究,想吃就吃。路上没有红灯绿灯,地里没有园艺园丁,水塘无人养鱼,蔬菜无人看管,一切都是自由自在地生长。孩子也一样。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父母多在城里忙于生计,爷爷奶奶又上了岁数,他们就只能自由地生长,甚至疯长。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更不值得炫耀,就如同村庄的远去、瓦房的没落和洋楼的崛起。或许有一天,村里人吃面时也不兴就大蒜了,甚至连面都不吃了,而是改吃比萨之类的,那就真是无可奈何了。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