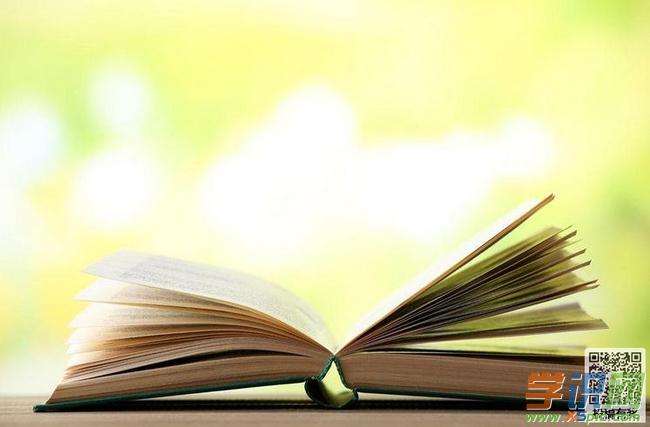生活随笔:我的第一次摆摊
摆摊记
很多从贫穷走过来的人,都有一份记忆是关于摆摊的。
我的第一次摆摊只能算是一个笑话。那是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把家里的小人书全部拿出来,模仿街上的书摊,在家门口把一根根绳子钉在墙上,然后把这些书依次挂起来,想租给别人看,赚钱。而要说的是,我家是在农村,村子里识字的也没有几个,所以,从市场效益来讲,这个书摊是不会有顾客的。几个小时后,在父亲的呵责下,我讪讪地收了摊。
二十多年后,我已是县城实验中学的一名教师了,经济仍然很窘迫,那时,我租的房子后面到了夜晚就热闹起来。那里有一个夜市,只要你在地面上摆一方长布,在布上摆上所卖的物品,然后蹲在那里就可以做老板了。所卖的商品琳琅满目,每天我在书房里码字时,耳边便充斥着小贩们的叫卖声和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声。
一天,我突发奇想,可以把家里那一大摞旧书拿出来卖。当我把想法说给母亲听时,立即遭到母亲的否定。“你一个实验中学的老师去摆摊,就不怕别人笑话?再说能卖多少钱?”我一想也有道理,以两元一本的市场价估算一下我那些旧书,总价值不会超过300元,于是,便只得作罢。
隔了没几天,我下班回到家,母亲兴奋而神秘地指着房间里一个大的黑塑料袋问我:“你猜,这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衣服,这么多?”
母亲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杨兰告诉你的?”“你这么大的包,一看就知道了,杨兰?你上她那儿拿内衣了?你要摆摊?”
杨兰是我的姨姐,做内衣批发生意,母亲提到她,那肯定是到她那儿批了内衣准备摆摊卖了。
虽然没有意料之中的给我惊喜,母亲脸上还是闪烁着激动的神情,她接着说:“杨兰一分钱没收,她让我先卖,卖多少再说,卖不了还给她!我明天准备先到附近乡下去兜一圈儿,看看生意怎么样?”
她顿了一下又说:“我想了想还是不在咱这后面摆摊为好,这里认识你的人挺多,说起来……难为情!”
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母亲已经在烧饭,那辆半旧的自行车斜倚在门外,满是泥泞。那一包内衣还放在房间里,除了表面有些尘土和拉扯的褶皱外,没有多大变化。母亲听到开门的声音,转头对我说:“回来啦!饭马上好。今天开市了,卖了一件踏脚裤,那人真刁,就几块钱的生意,还讨价还价了半天。我明天再转转,看来生意不好做。”
几天后,那些内衣大部分物归原主了。
再次摆摊已是四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到江南的一个小镇上做老师了,经济上较之前好了些。但当时在苏南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手头有点儿紧,我又做起了从童年时一直未遂的老板梦。这次被我看中的商品是玩具,靈感当然是来自儿子对玩具的痴迷,于是就从小商品市场批发了四百多块钱的玩具。见惯了儿子为获取玩具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以及作为家长的我们最后只能屈服的结果,我对卖玩具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当时所住的房子边上是个广场,到了晚上就有很多人来锻炼。我便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玩具中有一件是“小猴拉车”,装了电池后发出欢快的音乐声,那声音在广场上嘹亮地响着,“小猴”不知疲倦地奔跑着,成功地吸引了几个小孩子,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家长态度很坚决,无论小孩子如何的垂涎三尺也坚决不买。结果摆了几天摊只卖出一只2块钱的小跳蛙。无奈之下,我只得考虑转移阵地。偶然的一次,我发现晚上火车站广场那里的人很多。这一次,我和母亲,甚至还把儿子带去作为玩具模特,还别说,那儿生意真不错,我们刚刚摆了摊,就有几个小孩子和家长围了过来,一个孩子看中一个10块钱的玩具,我们刚交易完,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有人说,联防队的人过来了,我们一看对面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穿着制服的人员,母亲说:“不好!赶紧收摊。”于是,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玩具收上了车,然后逃命似的开着车跑了,我的练摊记忆到此画上了句号,那四百多块钱玩具最后自然都归我儿子了。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