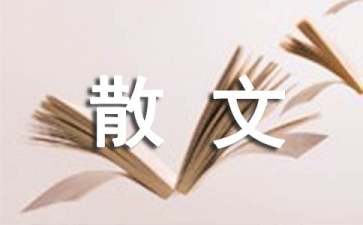经典散文:一个民族的尊严(12)
大河灯魂
他演小花旦翻身拐弯轻快活泼,恰似蜻蜓点水。他嗓音甜润,演唱时运腔婉转,吐字清楚。这些表演方面的技巧,为陈敬芝成功地塑造《游春》中的余香女,《小货郎》中的小姐,《送香茶》中陈秀英、渔姐、白海棠等角色。他们灯班在花鼓灯歌舞后加演小戏,并用“弦子”(民乐拉弦乐器)伴奏,故,人称“弦子灯”。由于陈敬芝、宋廷香、詹乐亭及玩友们经常在风台、寿县、颍上等地农村小集镇演出,“弦子灯”这种艺术表演形式,很快在这些地区流传开去。
一次,玩友们邀他赶四顶山庙会。到山顶后,赶会众闻听“一条线”来了。马上把他们的灯班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动弹不得,要求看“一条线”表演。人拥挤得打不开场子,陈敬芝只好在鼓架肩上即兴唱道:
庙堂庙堂好庙堂
姑嫂二人来降香
大嫂降香求儿女
奴家有话不好讲
众神灵你细想想
保佑我奴家有一个好夫郎
围观的人齐声喝彩。灯班子走下山去,群众跟着下山,走一段,停下来玩一回灯,唱几首歌。下山的路,到凤台不过三十里,他们竞走了一整天都没有走到家。“‘一条线一走,栽到九十九,回头一看,起来一大遍。”“听了‘小蜜蜂,无被管过冬;看了‘一条线,三天不吃饭。”从那时,这些话就众口传开了。
有次,殷家庙逢会。陈敬芝他们的灯班子刚到山下,只见山上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到处是人的海洋。拉洋片的、打彩套圈的,锣鼓声、卖小吃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上山的路早已被人堵塞,他们只好停在山下打锣鼓。有人发现了陈敬芝,高呼“‘一条线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山上诸多灯班及赶会的人蜂拥下山,把他们围起来。玩友连忙把陈敬芝顶在肩上坐着。拥挤中有人把陈敬芝的一只绿哗叽呢绣花彩鞋(此鞋系夏集一位热心观众赠送)抢在手中,他高兴得如获至宝,高举彩鞋呼喊:“一条线!一条线!”彩鞋在群众中传来传去,最后竞不见了踪影。
1940年,清泉乡丁毓铭等人请陈敬芝他们玩灯,演至半夜后,灯班要散场,观众不愿走,还是要求陈敬芝上台表演。他只好上台致谢,即兴唱道:
俺叫唱歌不费难
舌头打滚嘴动弹
唱到半夜三星落
唱到五更明了天
花鼓歌子没唱完
观众连声叫好,灯班子一直演至天明。
陈敬芝,真是火透了淮河两岸,他一到哪里,就被各类粉丝层层围住,就是不跳不唱,大家只要能看上他一眼,就能过上一把瘾,圆一个亲近“一条线”的梦。于是,但凡邀请他去演出的,不得不动用数个精壮大汉对他贴身保护,那戒备森严的架势,都是防备他不被其他村的粉丝,冷不丁地从他们手中将陈敬芝活活抢走。即便是在他巡回演出的旱地水路往返之间,不仅有保镖形影相随,竟连渡船的船舱,也用被子捂得严严实实。但尽管这样,这位在江淮大地、淮水两岸百姓眼中的“天下第一兰花”陈敬芝,还是经常遭到四邻八村的百姓不择手段的“抢劫”。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