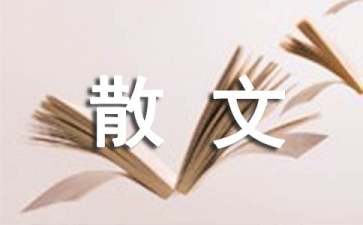经典散文:一个民族的尊严(27)
大河灯魂
李兆叶自14岁时跟本庄李兆富(别名“一条绳”)学玩灯,一年之后就变得深沉且谋定而动了。生性聪颖的他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多是听别人唱歌,看别人跳舞,一如既往地暗中留意揣摩和学习。时间长了,同班学玩灯的年轻人,李兆如(鼓架子)、李洪宣(大兰花)、李洪坤、李兆春、李洪本等,就根本追不上他了。操练几个月之后,他就“下场子”玩灯了。最初在本庄玩,后陆续到邻庄及毛集、刘集、肖庙、夏集、西成集、董刚、史集、曹集等地玩灯。他16岁开始出远门玩灯,先后到过双桥、窖口集、堰口集、石集、保义、隐贤集、众兴集等地。
李兆叶玩灯时扮演“兰花”,头上用撒包头(农村妇女的头巾)一围,上插球花(有时后边还安“架花”),上身着水红或水绿青年布大襟褂,下系插花缎裙子,这身打扮配上他匀称的身材,灵活优美的舞姿,当时令大姑娘、小媳妇们都自愧不如。
只要上了灯场,锣鼓家什一响,顿时他就精神十足,步法轻盈,动作敏捷,与平时生活中老实巴交的“猫春”判若两人。《小花场》是他经常表演的舞蹈,姿态表情富于美感,扇花、手巾花丰富多彩。他常用的扇花有单花、双花,以及很多说不出名字的单项动作。他舞灯有一个体会:只要玩的对手配合默契,乐队的锣鼓能敲到点上,他的动作就多,手巾花、扇子花就用不完。他的表演深受当地观众喜爱,桥口集的冯常春、保义集的常东升先后送给他两块“银牌”(特制的一种银质饰物,有链子可系胸前,下安有穗子和铃铛),三角寺的热心观众送给他两条裙子、一副“头面”(女人頭上饰物),以表达他们的敬慕之情。
李兆叶在玩灯的过程中,逐渐受陈敬芝等人影响,后改演“推剧”(当时还叫“清音”),常演的剧目有《白海棠割肝救母》《白玉楼讨饭》《安安送米》《贤媳孝公》《王林休妻》等。后又跟本族唱庐剧(旧称“倒七戏”)的五叔演《送香茶》,此剧让他传唱各地,使他名声大噪,妇孺皆知。
李兆叶嗓音高亢明亮,真假声结合得非常自然。在演唱“清音调”的过程中,他勤于钻研,广采众长,唱腔旋律丰富多变,虚字衬词顺其自然,他还能根据人物性格设计出多种性格化的唱腔。他所唱的“清音调”,每句前两小节大都能在高音区活动,自成一派,独具特色,在毛集一带,被人们誉为“猫春调”。从玩灯逐渐变成唱戏的过程中,李兆叶坚持在戏中运用花鼓灯艺术。他担任“花旦”上场时,仍手持扇子、手巾,上场、下场、上楼、下楼、观花走路、担水、划船等都用“游场”(叫“踩弦子”)。伴奏的打击乐器仍使用花鼓灯锣鼓,运用花鼓灯锣鼓曲牌。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