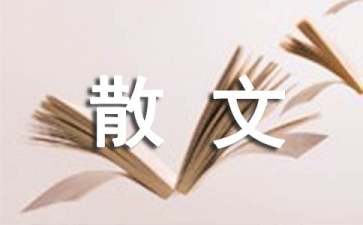经典散文:一个民族的尊严(33)
大河灯魂
而常春利的鼓瘾鼓痴,一点儿都不比当年的唐玄宗逊色。他学鼓击鼓时的坚忍和激情,台上台下手舞足蹈时的陶醉,魂从窍走时的双眼发直,手一沾鼓后的疯狂和忘我,简直让人以为神鬼附体。他四肢粗短,肚圆囊厚,身材敦实,一俟击鼓,眼如牛卵,嘴大如盆,呼吸带声,蹦蹬如蛙。加之他早年人穷无鼓,常用双手敲击肚皮为器,故,人们给他起了个极为形象的诨号:“老蛤蟆”。
贵为明代开国元勋常遇春后人的常春利家族,原本是当地富甲一方,远近闻名的钟鸣鼎食人家,但数代之后,因长辈经营不善,后辈挥金如土,加之淮河两岸灾难频仍,匪盗丛生,绑票杀人吃大户的强人比比皆是,于是到了他爷爷这辈,常家便家道中落了。原来的锦衣玉食、昔日的门庭若市、以往的良田万顷,已沦落到了坐吃山空、田亩卖尽、衣食无着的地步。赤贫的生活,长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艰辛,又在骨血里流淌着一代名将之后的傲气,使常春利具备了既有鸿皓之志,又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与深思熟虑的少年老成。他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是靠他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给大户人家做脚夫,到码头上给船家卖苦力、搬石头、挑水泥挣下的。如此重不负载的苦难岁月,既让他倍受煎熬,又刻骨铭心。他发誓,等他熬出头的那一天,他一定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重拾常家往昔的荣耀,重振常家的雄风。
如同古往今来的花鼓灯翘楚一样,常春利生活的环境,自然也是花鼓灯盛行的渊薮之地。从早到晚耳濡目染,博洽多闻的几乎全是花鼓灯。他的家乡怀远县,不仅是安徽省著名的花鼓灯集散地之一,他们村更是历史悠久,淮河流域极负盛名的大灯窝子。在怀远县所有玩灯人的眼里,穷人玩灯纯粹是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也是一种变相的精神解脱和放松。常春利爱玩灯成癖,自然是受当地风行的花鼓灯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与众不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和观看,而是深入潜心揣摩各家灯班的区别和独到之处。每当农闲,他白天放牛割草,晚上钻进灯场,就像一副狗皮膏药,紧紧贴住那些灯班子里的人和锣鼓响器,让人撕都撕不掉,竟一看就是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在对花鼓灯艺术各个行当逐一推敲,反复琢磨,又根据自己的身材外貌、力量劲道等综合考量之后,最终决定,他将以能使他血脉贲张、激情燃烧、大呼过瘾的“鼓”,作为自己终生不二的抉择。当他被自己这种终生无怨无悔的抉择,激动得泪流满面的时刻,他并不知道,花鼓灯的起源,竟然是先有“鼓”再有“锣”,后才有“乐舞”和“灯歌”的。当然,那时还是个“半拉橛子”的常春利,更不知怀远的花鼓灯形成,竟是始于上古时代“蛟龙会”的神话传说。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