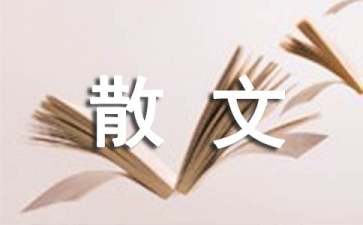经典散文:一个民族的尊严(34)
大河灯魂
相传很久以前,他家不远处淮河边上的荆山里,深藏着一条巨蛟。每到农历三月十五,它就会猛然蹿出洞穴,向人们索要牛羊猪狗。巨蛟在吃饱喝足之后仍不愿罢休,还要村里的童男童女以补元气,人们若是不给,便要吃尽所有活人,荡平两岸村落。但是,这个力大无穷的巨兽也有软肋,就是惧怕响器的震天动地。于是,人们在忍无可忍之下,于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齐聚大河岸边的荆山脚下,将用牛羊皮面做成的皮鼓,外加铜锣大镲、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动地,以此来恫吓这巨蛟,使其不敢出洞来祸害人间。久而久之,有人就将这一年一度约定俗成的“惊蛟会”,用上了锣、鼓、镲、跋等专用响器,再编上歌词,弄出舞蹈,形成盛会。史书记载,这便是怀远花鼓灯的原始雏形。而“老蛤蟆”常春利,对于花灯鼓给予他的启蒙与破窍,以及生命不息、击鼓不止的痴鼓,到底是天赋神赐,还是命中注定?看来只有天知地知了。
如同他同族的“一根筋”大鼓架子常和龙,他学灯鼓也是靠:偷、粘、跟、貼、磨、问,混合死缠烂打,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每当村里有南来北往的灯班子献艺,他总是早到多时,端着个板凳抢占有利地形和最近的位置,好在灯班演出时,能看清每一个演员的动作细节,捕捉每一个鼓佬和锣手的技术特征和节奏变化的起承转合,全神贯注地观察体味着各路打击乐手的动作、风格,以及鼓点轻重和音乐处理的微妙之处。直到灯班子打烊收摊离去了很久,他仍丢了魂似的蹲在原地,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
常春利小小年纪,痴鼓已成魔怔。但他家实在太穷,一日三餐尚不能为计,父母虽可怜这个早已在骨子里做下“鼓病”的孩子,但却高低拿不出钱来为儿子买鼓,更不同意他将来以鼓为生,安身立命,因为他们深知“玩灯的都是光蛋猴”这句俗话的分量,更知在江淮大地淮河流域,经年流传的“好男不玩灯,好女不玩春”这千古遗训的内蕴。他们虽是农民,却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死理。他们的梦想和所有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体体面面地做个上等人,替曾是如雷贯耳、威风八面的明代开国元勋常遇春宗族,重塑昔日的富贵荣华和光耀门楣。
但天生就是个犟种鼓痴的常春利,岂是他的父母打骂体罚,连唬带吓就能拗得过的。随着日月的流逝,体能和内心的强壮,他对鼓的悟性和激情与日俱增。他练鼓的想象力和认真,方式和内容,竟让他的父母、乡亲近邻匪夷所思。没钱买鼓,他就以肚皮当鼓;没有鼓槌,他就上树断干折枝自制工具;没有鼓点响动和节奏律动,他就以嘴仿音,以嗓促声。他遍访淮河两岸,方圆百里的鼓艺高人,绝不放过各路过往灯班的鼓技精活绝艺。他躺在树下打,蹚在水里敲,他仰在坟头上击。村头野地静态中的猪骡牛羊,他盯牢了瞅;邻里婆媳吵架骂街,他撵着看;屠夫劁驴骟狗,他目不错珠。淮水两岸的渔人船家、屁孩儿浑球泥塘里的互掐潜逃、水畔荷花芦苇叶上的落鸟蜻蜓、水中的游鱼青蛇、天上掠过的雁阵飞禽,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和悟性,全都化作他日后在肚皮上那轻重缓急、拍子节奏错落有致的敲击之中,直到将肚皮击打得青紫淤血,胀疼难忍时这才罢手。久而久之,他的肚皮上,竟被他自己击打出了一大块厚厚的老茧。这种闻所未闻的“练鼓击肚”方式,纵使访遍人间,恐怕也只有他常春利独此一家!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