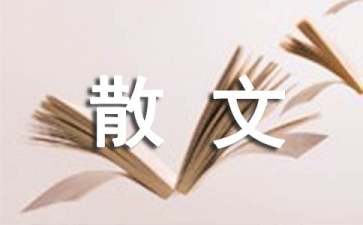经典散文:一个民族的尊严(35)
大河灯魂
孩子走火人魔地痴鼓,“以肚为鼓”的日久弥深,举手投足之间的鼓韵神采,卓异鼓手的品相初见端倪,常让父母热泪盈眶,又让他们犹豫不决。随着儿子的“肚皮鼓痴”亦加“病入膏肓”,终于使他父母早年的一言九鼎,在某一个时辰訇然崩塌。父母决定,让儿子拜自己的嫡亲三叔,本村名满江淮大地的泰斗级鼓手“三老望”为师学鼓。然,鼓手无鼓,一如战士无枪……
旧时的穷鼓手,大多都视鼓为命。再沾亲带故的鼓手之间,彼此关系再好的灯班子,无论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借人可以,借整个灯班子救场也成,就是不借响器。这个古老的习俗,不仅传代,更在千里淮河的八百里灯窝子里,似已成不必言明的约定俗成。有时,鼓手对“人鼓合一”的贴身爱物,已到了比老婆更重要的地步。鼓,除了鼓手自己,谁都不能碰。鼓手认定和迷信,鼓有灵性,别人碰了会有晦气。鼓若生气和不爽,它就没了精气神。在鼓手眼里,鼓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是确保全场演出成败的命根子,是花鼓灯演员“锣鼓提神,舞得带劲,锣鼓打焉,全都白玩”的命门。因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大鼓手“老三望”,虽是常春利的亲三叔,常春利又是对他九叩三拜的关门弟子,但无论传艺还是带他演出,就是碰也不让他碰一下自己的宝贝花鼓。但,常春利是什么人呵?十里八乡有名的“狗皮膏药”,方圆百里响当当的“甩不掉”!最后,老爷子在这个“老蛤蟆”小侄的软泡硬磨、死打烂缠之下,又加上自己年事已高,就不得不破例让他背鼓随同了。这下可乐坏了常春利,简直就把三叔“老三望”的鼓当作圣物,能为他心目中的“鼓神”背鼓,紧随其后到处演出,既能亲近花鼓,又能零距离观察老艺人击鼓,不啻是他人生中的一件极大幸事。从此之后,他不仅学艺更加刻苦,且时常将这鼓擦得纤尘不染,锃亮发光,随后又央求他娘省出口粮,咬紧牙关破费去县城扯回丝绒,为鼓缝上了人见人爱的紫红色鼓套……
但痴鼓之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鼓,诚如一个花痴对情人的暗恋,千言万语无从说出口;恰似一个骑术卓异的猛士,没有一匹独自拥有的千里坐骑,还怎样驰骋草原决胜千里?于是,不知暗自流了多少眼泪的常春利,突一日,作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太肯定的决定:“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尽快有一面属于自己的花鼓。”但,怎样才能拥有一面被他视为生命的鼓呢?那时,他不得而知。只是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面他梦寐以求的鼓。
那日,他的母亲让他挑一担白面粉,到蚌埠的市集上去换钱买米,等他担米回家下锅做饭。当他走到城里一个卖鼓的摊子前,就再也走不动了。他几乎没有问价,便用一整担的白面,从那卖鼓人手里换了一面他盼望已久的鼓和一双鼓槌。一路上,他像一个刚把新娘盖头掀起来的新郎官,一边打鼓,一路看鼓,一面亲吻鼓面,一边紧紧搂住鼓身,仿佛只要一松手,这面从此属于他的新鼓,便会一下子插翅飞丢。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换鼓的那担白面,竟是他们全家几个月的口粮。回到家中,他被气疯了的父亲按在地上,一顿牛鞭棍棒地好揍,揍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父亲揍他的时候,他哪儿都不护,只是蜷成一团,将那只崭新漂亮的鼓,紧紧搂在怀里,生怕有半点闪失。父亲看他护鼓连命都不顾了,喊叫着要将他的鼓砸碎,扔进灶里烧掉。这时,他母亲一把抱牢他父亲,并叫他快去他二舅家避难,这才救了他和那鼓的性命。几天之后,他家断顿,母亲背着全家,去当铺当了祖传的镯子,这才将这个伤未痊愈的儿子带回家来。一进门,他就冲着他父亲“扑通”一声跪下说:“爹,我往后再犯错,您尽管揍我,可就是不要砸我的鼓啊,它就是我的命。”常春利的父亲听完儿子的这番话后,一直沉默着……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