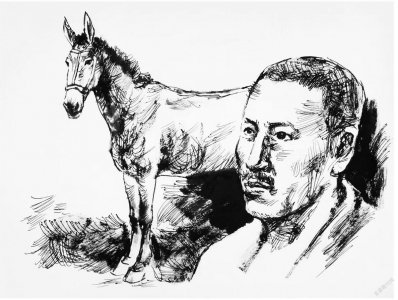小说精摘:在海一方(4)
在海一方
老路说,你路姐是替补队员。如果我或路西有事了,只能早点走,先把路姐和孩子送到学校,让路姐陪着孩子等学校开门。再送另一个孩子去另一个学校,这也是免不了。
3
老路父亲走的前两年,我就做社工了。老路父亲走后,老路把他母亲托付给了我。
从他父亲走了后,老路每年回来一次,探望母亲。我问他,没想过把大姨接去温哥华吗?老路说想过,可母亲不去,说贱土难离,说要陪着老头子,她走了,老头子在这儿孤单。老路抹了抹眼睛,大概又想到了什么。
老路又去了温哥华,母亲一人住郊区。临走时老路再次拜托我,抽空去看望他母亲,替他尽份孝道。我答应了。老路七十多了,像朵云似的,还在太平洋两岸飘荡,我看着于心不忍。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我又想起了这句诗。
我现在在一家叫羽航的社工机构工作,服务项目包括关爱老年人,尤其是孤老。像老路母亲这样的,子女在国外,孤老独守空巢,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身体硬朗的孤老,我们采取小组工作模式,带着老人们走出户外,参加集体活动。老路母亲九十多了,脚趾有点不适,不能走远。老人的听力视力也不行,参加不了集体活动。老人也不愿参加活动,宁肯待在家中,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我们启动了个案工作模式,一对一地进行心理辅导和援助。
我把老路母亲确立为羽航社工的服务对象,然后以工作的名义去看望老人,每半月去一次。老人如同生活在密封的世界里,我去了,像是打开了一扇门,老人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所以我每次去了,老人分外热情,话闸也打开了,说老路来電话了,说外孙和外孙女学习挺好,说路西给她买了件羽绒服。老人絮絮叨叨,我耐心地听着。等她说完了,我再说些外面的见闻,有时事的,有社会的,有街头巷尾的。老人有时听笑了,有时插上两句。我边聊边帮老人剪指甲、剪发,扶老人在院前屋后散步。老人有皮肤病,她手上没力气,我每次来了,要帮她搔上一阵子。
到了午饭时分,我动手做饭烧菜。老人不让,说我是客人。我说,大姨,别见外,您就拿我当您儿子吧。
老人真拿我当儿子了,每半个月了,就盼着我能来。我要不去,她很失落,像透不过气似的,站在门前的小路上,左顾右盼。我实在没个准儿,不是早两天就是迟一天。社会工作挺忙的,我的服务对象多是老人,老人们都有着强烈的被陪伴的渴望。小组工作容易些,做个案就忙不过来了,一对一的服务,很耗时。当然,我也乐此不疲,努力以一颗大爱之心,伴得夕阳红。只是对老路母亲,我深感歉疚,对老路也有歉意。答应了的事,却未能做好,不免有失信用。我在电话里和老路说了,老路在电话那端哽咽了,说,坤子,别这么说,我的义务你帮我尽了,我不只是感激,更多的是惭愧。有你关照母亲,我在国外踏实些了。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