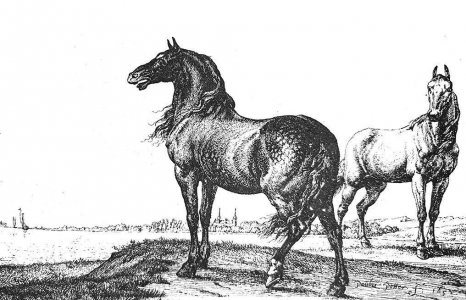精选文学:故乡思千里 霜鬓又一年(2)
故乡思千里 霜鬓又一年
我们徐家在芦滩圩埭的东头,再东边只有方姓一大家。与我祖父同辈,方家分為兄弟两户,一个叫学文,一个叫学武。徐家是兄弟三户:恒德、恒诚、恒安,恒安是我的祖父。徐家落户芦滩圩埭,到我父辈,只有三代。曾祖讳品南,我第一次知道曾祖名讳,是小时候从家里翻出来的毛章纸地契上看到的,祖父母那时也会念叨,哪块田、哪块地,是哪一年买的谁家的。
据老辈说,我们徐姓来自江对岸丹徒的小大港,老辈念作xiaodai-jiang,是大小港的方音。小大港位于圌山南麓,横山之东,但在父亲的印象里,他小时候从没有去过对岸,不能说清楚具体地方。曾祖是个医生,大概在清末民初,带着曾祖母一起到扬中行医,落户于此。村头的方家,曾祖辈叫方裕林,开了个茶馆,是新四军的据点。我祖父兄弟三人,大姥姥(大爷爷)有文化,常去方家茶馆,因此跟着闹了革命。我还依稀记得,跟大姥姥一起坐在祖场上晒太阳,听他嘚老经(讲故事)的场景,那是我最幼年的记忆。祖父则学医不成,开作坊,做生意,往返于江对岸的小河、埤城、姚桥,甚至丹阳,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耳熟能详,但感觉很远的地方。
我的祖母姓王,邻居称安奶奶,老家在老郎街西头港南。老郎街从前是丹徒、丹阳、泰兴三县交界,是扬中最早的集镇之一,离外婆家不远,我小时候常去。沿港一溜老街,石板路,两边是商店,铺板门面,跟江南的古镇相似,只是规模略小。后来因为远离公路,集市移到乡镇政府所在地,老郎街逐渐衰落,只留下不远处的车站还叫老郎。另外,我读书的兴隆中学,以前也叫老郎中学。
我的外公十三岁到上海学徒做裁缝,在上海滩为大户人家做旗袍裤褂。1949年以后,没有参加公私合营,一直自己开裁缝铺,为老客户手工定制。我小时候每年跟外婆去上海暂住,吴淞路407弄(又叫猛将弄)81号,包括周边的街区,海宁路、乍浦路、四川北路,还有外白渡桥、黄浦公园,旧时的模样,至今大多还依稀仿佛,如在眼前。十几年前我去过一趟吴淞路,弄堂仅剩半截,无复旧观。
外公姓王名钟明,外婆姓陈。外婆的娘家在另一个小岛上,现在叫西来桥镇,以前叫幸福公社,但通常大家都称中心沙。中心沙,在主岛最南端的江中,与主岛隔着一条夹江,与武进也隔着一条夹江,曾经隶属武进县,抗战期间划归扬中。往来扬中,要靠渡船,我小时候没有去过中心沙,后来有了趸船,再后来造了扬中二桥,才经常路过那里。扬中大桥通车,扬中人结束出门靠船渡江的历史,不过短短二十年。
外婆家的大圩埭,是我们兄弟和伯伯家的美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比芦滩圩埭还亲切。外公有一个兄长,也一直在上海,已经搬出大圩埭,到老郎车站附近,有特别大的竹园。与外婆家来往最多的是后面的大个姥姥(爷爷)、大个奶奶,大个姥姥姓张名恒松,年轻时跟外公一起在上海,亲如兄弟。当时已经回到乡下,传说扬中的日本鬼子是他带进来的(当然不是),是四类分子,开大会常被叫去搭台。外公晚年在上海,还一直得到大个姥姥的儿子(我们叫他高舅舅)的照顾。高舅舅的孩子,小时候在乡下与我们一起长大,现在还兄妹相称。隔壁张家有一个瞎姥姥(爷爷),很会讲经(讲故事),夏天在竹窠乘凉,围着瞎姥姥听他讲经,印象至深。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