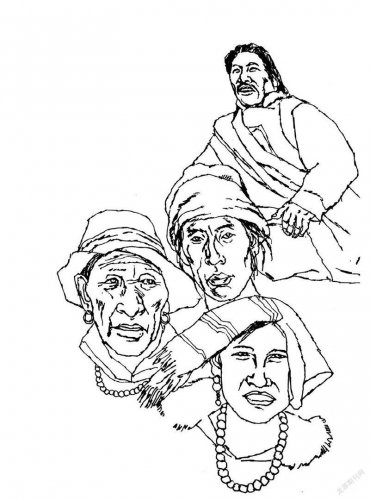生活随笔:特殊年代
父亲的砖厂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过完14 岁生日的第二天,天刚破晓,就听见父亲叫我。
我睁开双眼,隐约听到灶房传来母亲的哽咽声和父亲磁性的话语,忙穿衣,待走到灶房,眼前的景象却意外的静谧安然,只有老灶台炉膛里的火苗赶着锅盖间冒出一缕缕白色水蒸气,把玉米的清香飘满了灶屋。然而,那刻迷惘的我,还是发现了母亲脸上的无奈,看到了眼角涌出来的泪泉。
家里穷,买不起班车票,出门谋生全靠两条腿。第一天沿着312 国道,翻过古城岭,过了商州城,还没走到秦岭顶上牧护关,我的脚已起了泡,到了晚上,父亲只好陪我在距州城15 公里的陕西名镇板桥歇息。房东是板桥小学一位民办教师,看着我疼痛的窘样子,他绘声绘色地给我吟诵唐代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那刻,不知为何,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让我忘却了疼痛,也为我后来弃工从文留下了注脚。
待徒步到西安火车站,头顶上已走过了四个日头。好在那时“闹革命”,没钱买火车票的人都爬火车皮,就这么,跟着父亲爬上拉煤的货车,糊里糊涂地到了孟塬火车站,又穿来穿去半天,来到一处被大片庄稼地包围着的一孔砖瓦窑二间土瓦房前。
父亲一声:“娃子,到了。”自己顿时感觉有点失望。这就是父亲的砖厂?这就是家里人让我学艺谋生的地方。好在那天,天气晴朗,四野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苗儿在塬上劲风中摇曳着动情的掌声迎接我和父亲;好在那天,砖窑上空飘过的云彩,映着砖厂周围一片片金黄金黄的油菜花,风儿吹动阵阵清香沁人心脾。特别是父亲,满面春风,笑靥里的那个爽,满是窑场泥土的馨香。我还从来没有发现父亲这么高兴,这么兴奋过,压根儿也没想到父亲对砖窑的情感是如此的深沉。那一刻,我被父亲完完全全感染了。
其实,父亲是没有砖厂的,父亲的砖厂就是华山脚下孟塬土坡上一个叫冯家村的砖瓦窑。那晚,自己躺在土炕上,不知咋的,迟迟难以入眠,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屋梁上的檩条,从东数到西,从西数到东,满脑子胡思乱想,这就是谋生的砖厂,这就是学艺养家的地方,一孔砖窑、两间土瓦房和房子里一张土炕、三个储水大陶缸。我想若母亲知道这一切,不知道要为她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儿子伤心多少天。
人就这么怪,没有人跟钱过不去!一想到跟父亲学制砖能为家里挣钱,这砖窑是咋看咋美,土瓦房比老家的土瓦房还棒,就连三个大陶缸也咋看咋顺眼。就这样,一个当师傅的父亲和徒弟儿子,把土塬上一孔砖窑、二间土瓦房当成了家,父亲成了管我的师傅、给我做饭的“男妈妈”。后来,村上一位和父亲一样会做砖的冯伯伯带着他的儿子仁义来了,砖厂一下子有了两个师傅父亲、两个徒弟儿子,场子上也热火了起来。再后来,冯伯和仁义也搬进了土瓦房,父亲和我有了伴,晚上的土炕也热火了起来。要知道,那年头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也看不上报纸,在荒土塬上有一位同龄伙伴,对我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天蒙蒙亮,我俩一块起床,一块为师傅跑砖斗子,一块用架子车拉着塑料桶,从五里外的司家拉回做饭用的水,储放在三个大水缸中。到了晚上,还能爬上窑顶望着北斗数星星。没过多久,砖厂成了我生命里的一切,特别是学习父亲手工制砖的绝活,日子虽苦虽累,但干得很爽很快乐。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