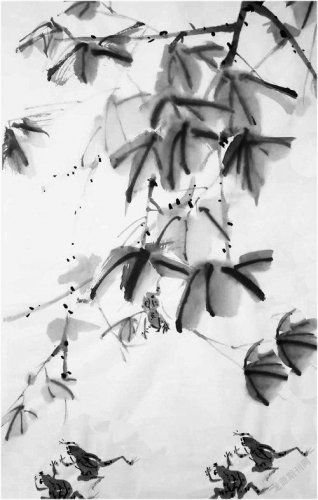生活随笔:后来的故事(2)
你好 记忆
董文不插话。方之不是在征求意见。
“你是写小说的,小说就是编写另一种人生。你出书,我有什么?活这么大年纪,留下什么了?”
公园不远。公园大门口是一棵大榕树。公园是新建的,取名“大榕树公园”。园内没有大榕树,唯一的一棵在园外。有点错位。小时候他俩经常在树下玩,在树根上爬,后来,坐在树根上看书,复习功课。
那时候,大榕树就很老很粗很高大,现在也是很老很粗很高大,看上去没有两样。小时候见过的场景都会随着年龄和眼光变小变窄变矮,这棵榕树的生长与他俩的年龄、眼光同步。
只是有一天他们不在了,榕树还在。两人这时都这样想。
董文天天路过大榕树。“平生一蓑风雨,老树最是莫逆交。”他写这样诗句。欢乐时走过,痛苦时走过。柳烟成了方之的妻子,他曾在树枝中寻寻觅觅,找一个上吊的枝丫。“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忽然想起这句俗话。人生是棵树,长满许许多多可能。成长,便是像树一般经历春夏秋冬。他终于明白了。
快要告别人间的方之,他不知道大榕树的枝枝杈杈对董文意味着什么,大榕树下的小路对董文意味着什么。
“去树荫下面。春天阳光紫外线强,让皮肤细胞里的活性氧增多,皮肤老化得快。”
董文笑笑。方之和他的脸上早就搁挤不下更多的皱纹老年斑了。方之改不了发号施令,越老越喜欢。坐轮椅享受发号施令有合理性了。
“算了,进公园。左边有个茶室,当初是关帝庙。”
方之自個儿笑了,“是你本家。你该记得的。”
董文没有想过。马上记起来了。
毕加索说,我用一生的努力,只是想回到童年。
董文路过大榕树和关帝庙时也应该这么想的,毕加索的话是回到单纯、天真的年代。世事纷乱,董文操心和应对的事太多,回不去。
不过,这里的童年实实在在。他和方之上小学四年级,10 岁,迷《三国演义》。他和“刘备”——杜方之,还有位“张飞”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三人同喝一碗香灰水。“张飞”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书,两人都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他俩也想不起结义后有什么壮举。便是童年。
童年玩伴多半是近邻,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他俩小学、初中、高中一个学校。上小学,方之家有钱,开油坊,后来父亲吃喝嫖赌败了家。董文父母则省吃俭用,买地置户成了地主。上高小,方之的学费董文家交的。上中学,翻了个,方之家评上城市贫民,很神气,董文家败了。他俩都爱看小说,方之买的书多,四大本《静静的顿河》都敢买,他父亲说看完了别丢,纸张可以包肉(他家开肉铺)。董文只能买薄本的,如苏联电影剧本《乡村女教师》。两人一起看,不分彼此,不计厚薄。高中毕业,两人一文一武各自飞。董文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报社,方之军校毕业去野战军炮兵部队。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