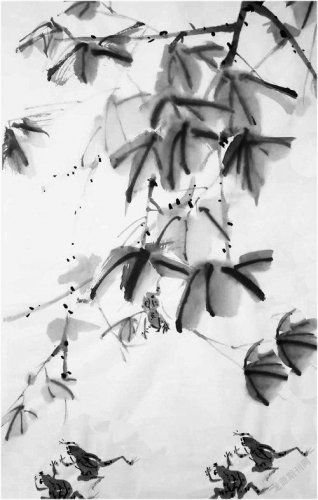生活随笔:后来的故事(7)
你好 记忆
方之又倒了一杯酒。董文只顾听,心怦怦跳,忘了劝他别喝。
“后来,三封信让柳烟看了。”
“我听说了。”
“你听谁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怎么会知道?”杜方之清醒起来,认真地问。
“说重点。后来呢?”董文严肃地提醒,“什么时候让她看?为什么让她看?”
军宣队进驻报社不久,奉命恢复报纸文化副刊。
副刊的原诗歌编辑“文革”之初便跳楼自杀,醮血写下“我欲乘风归去”6 个字。董文兼编诗稿,诗稿很多,每天几乎占报社总来稿的三分之一。他在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柳烟的作者,在当时打打杀杀的千篇一律的诗稿中卓尔不群。通信地址是街道工厂,工人。当年只有工农兵的作品才可以发表她的诗,他编发了几首,连报社的同事都喜欢。于是去信,约了她。
柳烟来编辑部了。白衬衫工装裤,剪短发,大脑门,浅浅的笑。眼白泛蓝,瞳孔发亮。头发上散发一股清香,也许是“浑身”。董文承认,一下子被迷住了。
“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这是他应该问的。
“徐志摩,泰戈尔。”她很勇敢。
“你多大了?”这是他不应该问的。
“28 岁,”她回答干脆,“10 年前高中毕业,考大学家庭出身政审不过关。我爸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湘西会战阵亡,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你知道湘西会战吗?”
“没听说过。”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
“抗日烈士,共产党是承认的。”
“你真好!我的稿子还能发表吗?我在厂里糊火柴盒,干了6 年,老工人了。你看我手指多粗!我还是要考大学。你知道大学什么时候恢复招生?多老了我也考,考中文系。我一直在看书,复习功课,你信不信?”
“你会成功的。”
这样单纯,这样清新,这样有理想有目标。董文这样想。临别和她握手,她的手并不粗糙。这感觉一直记得,他也奇怪。不粗糙的手。
半年后,董文带她去见杜方之。
“多大了?”杜方之也问。柳烟回答。他不相信:“没那么大吧?看上去最多25 岁。”
董文三言两语介绍了她。方之并不注意听。董文和柳烟还站着,她和方之一般高。
“工人,很好。”
方之说了一段毛主席教导,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之类的话。不再说下去了,自己也觉得无趣,柳烟怎么看也不像工人阶级。她只是在老男人老女人成堆的地方掺入青春的气味。
“就这样吧。你们工厂我让人事部门去打个招呼,今天星期四,下星期你就来编辑部上班。董文同志负责安排桌子、领稿纸、领文具,有事你可以直接找我,报社行政部门官僚主义严重得很。”
相关阅读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