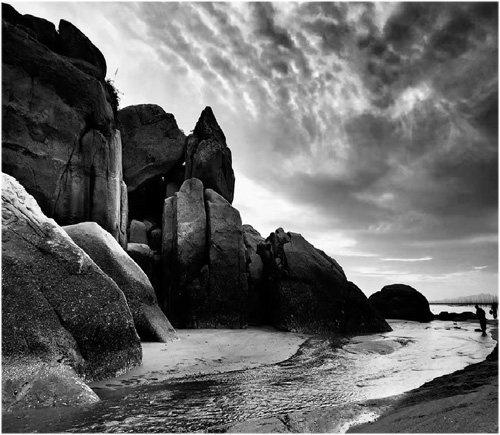生活随笔:矾山随笔(2)
矾山细节
如果记忆中的矾山依然是一株参天大树,那我蛛丝马迹的细节回想就像沿着叶面上的脉络的沉浸,它通过枝丫、树干,终于到达根系和土地。
我出生的地方是矾山镇最热闹的街道边,当时叫第四居民区,现在叫新华街。我父亲的老家在古路下村。古路下张氏是矾山最早的先民之一,参与矾山明矾采炼,比较有名的是创办了位于深垟茶山宫的炼矾窑,他们是矾山公认的翻窖好手。他们组建了一支搭建炼矾厂房的队伍,建矾窖,搭厂房(材料用毛竹、茅草、稻草),因技术过硬,搭建的矾窖牢固耐用,赢得矾山各界称道。翻窖是好身手,抬石也是很内行,古路下人对待几千斤矿石不在话下。矾山乡贤、民俗博物馆主人朱良越小时候就多次看见古路下人合力扛着巨大的机械、车床从南垟312 矿硐一步一步运往414、502,甚至更高的山段。1947 年,张韶武编著的《平阳六年》有记,古路下人张子芬担任矾山挑矾工会会长。苍南、平阳两县著名文化人、现年91 岁的郑立于先生在《矾山中心小学筹建新校舍纪事》中也提道:“厂工工会林培植、挑工工会张子芬、矿工工会卢兴谦、矾商会朱璇及工商联的庄步法等为建校出了大力。”这个从古路下出来的挑矾工会会长,因为不识字而枉入一场案件。龙泉劳教回乡后,躬耕田野。我至今清晰地记着,在矾山柴桥头的溪滩边,这个老汉顽强地开出一小块杂地,不论春风夏暑、秋雨冬寒,这个半驼老人总能种出多少不一的蔬菜和花果。
我当然记得很牢,因为他是我爷爷。我父亲老年时也有点痴呆,在生命最后几年的多次来回出走中,古路下是他永远不曾迷路的地方。
现在,村庄被新建的230 省道分成了两半,所有道路都是水泥做的,比水泥还生硬。村里一座宗祠香火常盛,它比香火还柔软。
我大姐18 岁时从矾山街道边嫁到福德湾山上的南山坪旗杆内朱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矾矿当工人是很吃香的。姐姐结婚时,我父亲给她的出嫁礼中就有“蝴蝶牌”缝纫机等物件。那时我上初一光景,我一有时间就跑着上山,到姐姐家蹭饭吃,而且还有点心。记起某次中饭顶撞父亲后,为躲避母亲的惩戒,我拔腿就跑。从现在的矾山新华街我家,经过福德湾村,一路跑到南山坪旗杆内大姐家。因为学校有上课,我只躲了一天,第二天就垂头丧气地回家了。那天晚上,母亲把我拉起来,拿出事先准备的笊梳,狠狠地打我屁股。几分钟后,一旁无语的父亲过来拿走我母亲的笊梳,说,辉下次不会了。
前几天闲走,我用半个小时数清从南山坪到福德湾的石台阶有936 级,从福德湾到矾山内街有627级。少年的我啊,在这条昔日的挑矾古道上欢快地跑上去不到一刻钟,跳跃着走下来还不到十分钟。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那些关于蝉的记忆
廖锦海 对于蝉,我历来不是很厌恶,但也不大喜欢,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清晨,好不容易趁凉快睡个懒觉,栖息窗外柳树上的蝉儿竞争先恐后放声高歌,仿佛一支乐队在演奏高亢激越的曲子,我
-

生活随笔: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
燕茈 1 夜半,周围静悄悄的。 小乖每天夜里都要哭醒几次,醒来就坐在床头,对着嫲嫲的房间哭喊:“嫲嫲,阿嫲嫲。”(嫲嫲,是客家方言中对奶奶的称谓)直到嫲嫲过来,喊句:“组惹(
-

生活随笔:父亲的一辈子
十多年前,我把父亲从江西老家接到深圳生活,想尽儿子的一份孝心。但父亲对喧闹的城市总是有些不习惯,再加上方言太重,很难和他人沟通,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
-

精选散文:肝胆相照的友谊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7年7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今新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